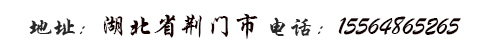田园将芜,人类终将无所立足于自然之间
|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十几岁少年时朗朗上口的句子。 教科书挑选的古文典范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情感、生活赖以进退取舍的依据。但是,十几岁的少年,稚嫩单纯,生命才刚开始,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可以领悟了解陶渊明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高唱「归去来兮」的深刻意义吗?如今,青少年时背诵琅琅上口的记忆还在,读起来却是完全不同的领悟了。 陈洪绶《陶渊明画卷》 很多人写陶渊明故事,我最喜欢晚明清初画家陈洪绶(老莲)画的一个以陶渊明一生为故事的画卷,其中也有「归去来」一段。这个卷子收藏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艺术博物馆(HonoluluMuseumofArt),三十年前曾经为了看这个卷子,特别飞去檀香山。 这个卷子依据萧统〈陶渊明传〉为蓝本,把渊明一生绘成十一段故事:「採菊」、「寄力」、「种秫」、「归去」、「无酒」、「解印」、「貰酒」、「讚扇」、「却馈」、「行乞」、「漉酒」。 陈洪绶曾经活跃於民间画像的制作,他摆脱了宋元以来文人太过洁癖清高的限制,亲近许多可能被文人看不上眼的民俗造像,像庙宇画工的壁塑剪黏土、,像民俗年画稚拙谐谑的表情,不求写实,却在晚明清初独树一帜,在一片僵化的文人窠臼中开闢出新的美术格局,创造出极具个人特色的美学风格。 明亡之后,陈洪綬有短暂的消沉,自号「悔迟」,但很快似乎看破兴亡的政治骗局,又恢復他旺盛活泼的创作。 我喜欢清人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说的故事,清朝入关,大军南下,在浙江抓到陈洪綬,胁迫他画画,「刃迫之,不画」,刀架在脖子上,不画,但是「以酒与妇人诱之,画。」 陈洪绶真实活着,画真实的街市百姓,他笔下的陶渊明也真实活着,爱菊花,爱酒,即使「归去来」,也毫不作态。 写〈陶渊明传〉的萧统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贵族,身为太子,侍母至孝,济助刑余贫苦人,熟读《金刚经》,做出「三十二分」,编《昭明文选》,影响后世巨大。而他著述的〈陶渊明传〉更是提纲挈领勾勒出南朝一个特立独行人物的生活面貌。 陈洪绶依据萧统的文字,一段一段做成绘本,陶渊明的事迹,有了画面,更为鲜明活泼。从陶渊明到萧统到陈洪绶,一千年间,恰好贯穿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平庸妥协的独立传统。「独立」不是作态,「独立」是内在世界有足够的自信,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蝇营狗苟,自然活出自己的真实面貌。 採菊 我喜欢陈洪綬笔下陶渊明的「採菊」,「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名句,说的不过是家边篱笆下的菊花,心境悠閒,山水就在眼前。 「採菊」更依据萧统的文字描述:「尝九月九日出宅边丛菊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这裡说的「弘」是江州刺史王弘,王弘一直想结交陶渊明,渊明不太搭理,王弘还是彻底「陶粉」,照样常送酒给渊明。 画里的渊明真的是「满手把菊」,像要把菊花的香塞进身体里去。陈洪绶笔下,渊明梳了奇怪的头,很时髦,人物造型可爱活泼,不迂腐,不道貌岸然,充满现代感。渊明手持一束菊花,凑到面前闻嗅,神态可爱。他脱了鞋,坐在磐石椅上,旁边有一张琴。渊明不解音律,但有无弦琴一张,没事就弹弹弄弄,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比起附庸风雅者,渊明更懂什么是真正的音乐吧。 「田园将芜」 「田园将芜」,归去来兮后的第一句,中学考试时不假思索知道这句怎么考试,怎么回答。现在重读,重重疑问,不断问自己:「我的田园在哪里?」我无法回答。 生于战乱的一代,离乡背井,没有土地,成年后,在许多大城市流浪,脚下从来没有一块自己的土地。 再回看四周,现代城市居民,有几个人拥有「田园」? 渊明高唱「归去来兮」的时候,很篤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园。但是,现代人的「归去来」,一开始就是困境,「田园」究竟在哪里? 「田园将芜」,是气候的变异,是巴西、澳洲的森林大火,是北极的融冰,是各种动物昆虫的濒于灭绝,是各处豪雨不断,土石流氾滥,是印尼的洪灾,是岛屿日復一日解决不了的霾害,是海平面上升,危及许多三角洲城市居民生存…… 「田园将芜」,深层思考,是不是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剥削自然,恶性资本市场无节制开发,物种不能延续生存。沾沾自喜於经济指标,结果是「田园将芜」,人知识分子离开了土地,像陶渊明,走向职场,有一天,发现土地荒芜了,有了回归土地的向往,高唱「归去来兮」,那是今天重读「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深沉意义吗?类终将无所立足于自然之间。 「胡不归」,问得好,我们还有回头的可能吗?我们还找得到回归自然的路吗? 也许应该好好看看陈洪绶笔下的陶渊明如何「归去来」,「归去来」自是有来去的因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xianga.com/cxgj/13654.html
- 上一篇文章: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房价这些房子不能买了
- 下一篇文章: 火箭大胜快船豪取两连胜哈登三节不到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