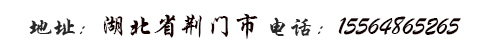误南墙上
|
(一) 九月秋雨绸缪,般若寺阴冷森寒。 我跪在佛前,又深深磕了个头。 “皇后为国祈福这般用心,当真是我太雍国之幸事。”随行的掌事太监尖声奉承着。 住持玄净在一旁安安静静看着,一双年老浑浊的眸子平静地注视着我。 我不敢抬眸看他,我怕他看清我所思所想。 我仍跪着,跪在佛前,手上握着的香几乎已快燃尽,我也没有站起身来,把香供奉至佛前。 宫女小声道:“娘娘,快起身吧,您已跪了一个时辰,连这手上的香都换了几炷了,佛祖想必已经看到您的诚意了。” 我摇了摇头,没有做声。 “皇后快快请回吧。”住持玄净终于开口,声音沉重悠远,“再不走,这风雨可就要来了。” 他红色的僧袍落到我眼里,是风沙侵袭的颜色,像极了十年前狂风席卷的大漠。 我的心揪了揪,又重重磕了个头。 佛祖,你当真知道我所求何事吗? 为这国泰安康,还是我一己私欲。 香不知何时燃到了尽头,星星点点的火灼了我的手,我一个吃痛刚想松开手去,已有一双素白的手落到了我的身前,轻飘飘将那半指长的香接住了,纤长的手轻轻捧起那仍旧燃着熠熠火光的香,慢条斯理地将它送到了佛前,送进了香炉。 寡淡的檀香味带着风,从他素白的僧袍里溜出来,钻进我的鼻子里。 我埋着的头还磕在地上,青石板砖是冰凉的,指尖上的灼热也只是一瞬,但这么跪着,叩着首,在这萧瑟秋风里,我却突然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温度。 (二) “施主往后莫等香灼了手,才知晓要松开。” 从佛前传来的声音,清冷的,像三月春雨淋漓下的荷冒出尖尖角的声音。 我抬起头,缓缓看向他,面上不敢露出一丝表情,宽大宫袖下的手却颤抖地不能自已。 “谢……圣僧指点。”我说。 他平静地转身看向我,宽大的僧袍是素白的,琥珀般的眸子里印着我的模样,锦衣华服,雍容华贵的模样。 我跪在他面前,看着高大的他,高大如身前巨大佛像的他,沉默的,了无生机的模样。 他终究还是来了。 雷就在这一瞬间炸开,雷声裹挟着霹雳般的暴雨轰鸣而至,风雨侵袭,天地晦暗。 我打了个寒颤。 雷雨天,我向来是怕的。 “娘娘,咱们该启程回宫了。这天色也不早了,看样子,这雨一时半会儿只会越下越大呢。”掌事太监出声提醒道。 我回身看了看般若寺外,雷电交加,林木飘摇。 “今日便请施主一行人在此宿下吧,外头大雨滂沱,出了事只怕诸位也不好交代。”他突然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 “这……”掌事太监犹豫道。 玄净住持这时道:“风雨这般大,当下,诸位便是想走也走不了的。不如便在此宿上一宿,明日启程。般若寺乃皇家寺庙,还请诸位安心。” 我起了身,酥麻的双腿有些不稳了,我却仍要端正了身子,高高昂着头,轻声应允道:“如此,便叨扰圣僧了。” (三) 玄净住持伸手指了指南方客房,道:“皇后请随我来。” 一旁的宫女已备好伞,候着我往客房去。 我提起宽大的裙摆,在原地顿了顿,看了看外头,有些犹豫。 “贫僧新得一卷古佛法,不知施主可有兴趣在此与贫僧探讨一二?”他突然轻声在我背后这样说道。 我几乎是立刻便回了身,重重点头道:“好。” 玄净住持沉默着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这才挪开了步子往外走去,红色的僧衣晃进风雨里,一步一摇,直到连他的背影都被雨吞噬了去,我才听到他沉重的声音从远处缓缓传来:“这风雨啊,怕是难歇了。” 随行的宫女太监们很快便都散了去,只留我与他二人在这大殿之中。 他仍站在佛前,背着身,燃起了一炷香,香烟缭绕,檀香味寡淡。 我在他身后,听着雨声淅淅沥沥,和他宽大僧袍衣料摩挲的声音。 “顾灼。”我喊。 (四) 他捧着香的手顿了顿,片刻,才将香奉至了佛前。 “贫僧法号南拂。” 我笑了笑,说:“好久不见。” “嗯,许久不见。”他说。 “十年零三个月。”我还是在笑,一边笑一边说。 “十年零三个月再五天。”他终于回了身,看向我,声音平淡的好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 雷又轰隆炸了一声,不知为何,笑着笑着,我便哭了出来。 “还是这般害怕雷雨天吗?”他说,握着佛珠的手招了招,“往里面来些。” 我低下头抽了抽鼻子,往前挪了两步,笑道:“你还记得。” 他没有说话。 (五) 我又朝他走近了些,直到走到他身侧,站在佛像下,被冰冷的佛像俾睨着。 “堂堂天雍国的第一圣僧,六根不净哦。” “净不了了。”他突然笑了笑,并不看我,只是静静看着那缓缓燃烧着的香火,淡淡道。 “那又当如何?”我问。 “便且认命。”他说。 我冷声笑了笑,拂了袖走到一旁,背对着他,问:“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大漠里,我问你该当如何,当时你是怎么回答的么?” 他看了看外头,沉默许久,才说:“雷声歇了,我送你回房吧。” “圣僧不是还有古佛法要与我探讨一二么?”我明知他是知晓我害怕雷声,才将我与他留在一处,却偏生要这样问。 “已探讨完了。”他说。 “什么?”我问。 “又当如何,便且认命。”他轻声答道,素白的手撑起素白的竹骨伞,走进了雨里,而后立在风雨里,回身看我。 (六) 我笑了笑,看着风雨里穿着一身宽大僧袍的他。 氤氲的雾气里,他眉目英朗一如十年前的模样,只是那时的少年,他不叫南拂,他叫顾灼。 他曾鲜衣怒马,意气风发,曾单枪匹马平定南戎叛乱,也曾为博红颜一笑掷金千万。 顾灼,那个顾灼,和如今这个神色平淡,淡泊如水的僧人,也许当真是两个人了。 厚重的冠发压得我脑袋很沉,我低着头想了许久,才提起笨重的裙摆,朝他走去,走进风雨飘摇里唯一安稳的伞下。 靠他很近,他并不避讳,寡淡的檀香味将我们包围。 雨声很大,我们走在湿漉漉的地里,什么都听到了,却又什么听不到。 他的呼吸他的心跳我都感受不到,只有雨声风声虫鸣声传入耳中,这般若世界的万物都是有声的,唯独他,我听不见他的声音。 “今晨,我奉旨来般若寺为国祈福,在入大殿上香之前,玄净住持先将我叫了去,与我讲了一番话。” “师父?” “嗯。总归我与玄净住持在我入宫前便已相识,他老人家当真十年如一日的对我好。” “师父他向来如此。” “你便不关心住持与我讲了些什么吗?” (七) 他顿了顿,才道:“你若想说,自然会与我讲。” 我低低嗤笑了声,“你如今这个不温不火的性子,倒不如从前可爱了。” 他沉默着没有应声。 过了许久,才轻声道:“前面左拐,便到了。” 我看着面前不远处的一堵墙,道:“若是不左拐呢。” “右拐的话又要绕一大圈才能回来。”他说。 “我是说,如果一直往前走呢。”面前的那堵墙越来越近了。 他踩在雨里的湿漉漉的脚步就这么突兀地停了下来,风声雨声虫鸣声这一瞬间都静默了,只有他的呼吸他的心跳落入我的耳中。 急促的,扑通的,他的声音。 他果然没有忘记。 (八) “再往前走,便要撞了南墙了。”他说,声音清清淡淡的,像细雨落在荷叶上,又滴答落入水中的声音。 “那又该如何呢?”我问。 他湿漉漉的步子顿了许久,才终于又提了起来,“不打紧的。”他说,撑着伞的步子没有半分迟疑,随着我往那南墙走去,“撞了南墙,便知道要回头了。” 这话说的轻轻巧巧,我突然想到十年前大漠孤烟里,他提着剑将我护在身后,高昂着头说出那句话时的神色。 彼时烈日灼灼,他的剑沾染了许多斑驳的鲜血,在阳光下炙烤出铁锈般令人作呕的气息,他直着背站在我身前,高大的身子替我遮住了灼人的日光,也替我挡了数不清的刀光剑影。 身前是重兵包围的生死阵仗,背后是深达千尺的悬崖峭壁。 他那时却没有显出半分颓唐来,一双眼像大漠的鹰一般锐利,护住我的手掌心里有滚烫的温度。 “便是撞了南墙,老子也不回头。”那时的他,是这样说的。 那时他话里的决绝和着大漠的风沙,深深砸进了我的心里,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不管你是顾灼,还是南拂。 我不会忘的。 未完待续 阿湫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xianga.com/cxpz/3595.html
- 上一篇文章: 重磅快去许愿崇庆寺高僧在新余设
- 下一篇文章: 白落梅我不去寺庙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