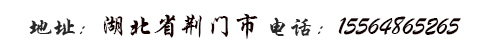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檀香刑中弥漫
|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文本中,作者向我们叙说了高密人的原始生命力,一种“坚韧”的生命意识,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意识,他们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苦与乐,为了存活下来,他们会顺应自然,坦然的接受苦难,其坚强的忍受力让人心生一种敬佩之情。 莫言在《檀香刑》中是这样介绍这类人身上坚韧的生命意识的,尤其是在面对马桑镇惨案时的人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是这样描写的“这一夜的马桑镇彻夜不眠,女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棺材铺里的斧凿声一直响到天亮”,但在经历了亲人间的生死两隔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做人还是平凡点好,争这个争那个,兴许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性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于是《檀香刑》中又是这么记录了二十天后的镇上出现的和谐场景,“黄昏时,镇上的人都遵循着老习惯,端着粗瓷大碗在街上喝粥……吴大少爷的话向来都是云山雾罩、望风扑影,人们半信半疑地听着,权当下饭的咸菜”,可见二十天以后马桑镇的百姓们回归现状,忘记苦痛,继续活着了,在面对村民们惨死的沉痛打击后,让他们更加意识到了能保存性命活下来的艰辛与不易,进一步衬托出了“活着”的弥足珍贵。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也就是只有存在的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而这个“尺度”是通过具体而并非抽象的生命形态来体现。这也告诉人们“活着”才是生命的最根本价值和最真切目的,而生命的根本价值就应该以“活着”的生命形态为基础,因为如果生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那生命的其他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当自身的生命惨遭灾难性的打击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活着”,然后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选择了向生活与社会妥协。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那种乐天顺命、知足常乐的坚韧与通达。 这也是一种坚强而又孤独的生命意识,对生命价值和目的有着全新的认识、对苦难的正视与超越有着独特的理解,一方面就算身处困境,他们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调整一下,仍怡然自乐;另一方面,他们是孤立无所依,无论是当地官员还是山高皇帝远的统治者都没人会真的去为他们讨回公道,这尴尬的局面为了要存活下来,使他们不得不学着适应并坚强应对。 总而言之,这种坚韧的生命意识,无不在述说着生命的悲哀,但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他们心里仍是坚守“活下去,怎样都要活下去”的信念,对他们来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因为最真切的“活着”才是切实的存在,意味着生命可以继续,那么我们“活着”就不应该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在对人生的悲哀和世界的残酷完全理解、认识了以后,以一种不惊不喜的态度和波澜不惊的心情来对待生活。在人们遭遇苦难后的那份从容不迫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生命本身芥子须弥般的力量。 余华曾说:“《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面对苦难时的那种乐观旷达及其顽强毅力,正是中华民族虽历经千难万险而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活着的人在面对亲人逝去时的痛彻心扉,既彰显出了对生命的关怀,又反映了他们选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忍耐来抵抗外部世界对自身生命的压抑。在面对马桑镇惨案时,由于他们无能为力,所以只能忍耐,用这种方式向社会做出了妥协,但他们又心有不甘,私底下为孙丙凑盘缠,帮助他逃离魔爪,也间接把心中渺茫的希冀寄托在孙丙身上,可见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向社会妥协,被悲痛麻木化了。显然他们也知道唯有继续活着,生命才会有意义,虽然目前他们选择默默承受了生活中的这一切,并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苦与痛,但这也为他们孕育出了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xianga.com/cxxw/15150.html
- 上一篇文章: 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的融合檀香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