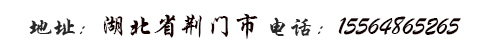李敬泽小说艺术精神的一次ldquo认
|
北京白癜风哪里医院好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生死疲劳》初版于年,是莫言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莫言仅用43天便写就了这部作品,但这个故事却在他心里酝酿了40余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自年推出“莫言长篇小说全编”系列以来,这套书以全新的装帧和高质量的编校水平,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生死疲劳》曾入围年首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荣获年“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年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奖项;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榜。年初,为感谢读者对“莫言长篇小说全编”的喜爱,我们在全新修订的基础上,对书籍的装帧设计、配色方案和封面纸张等进行了升级改版,新版本现已在各大网店有售。 《生死疲劳》 (修订升级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先生,他在阅读《生死疲劳》后,这样说道:“《生死疲劳》是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之伟大传统的致敬之书,是小说艺术精神的一次认祖归宗。”“大我”与“大声” ——《生死疲劳》笔记之一 文 李敬泽 一 一个冤屈的厉鬼在大地上游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由此开始。 对这个鬼,我有一系列问题: 他是谁?当然,他名叫西门闹,是一个在历史大变中横死之人,他因他的身份而死,但在自然法的衡平之下,他其实并无死罪,他甚至是个勤劳善良的有德之人。 由此,莫言似乎是承袭了中国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浩大的历史意志与渺小的个人命运。历史无所不及且不加拣择,个人无所遁逃而孤弱无告。 在这个格局之下,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冲动就是在历史的轰鸣中寻求和倾听个人的声音,这是自我倾听和自我倾诉,是要回应和求证一个现代问题:我是谁? 正是在这个地方,西门闹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想象中他的无数同命运者分道扬镳。他完全不为“我是谁”的问题所困扰,对他来说,他是谁是天经地义、毫无疑义的,他是乡村经济、文化、伦理生活的中心,是承担“天道”之人,他的全部生活具有一种“自然”的正当性,如同四季交替,春种秋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推动着他的那种“冤屈”,那是被“天道”所遗弃的冤,是天地不仁的屈;这个人的根本困境是,他有所信,这种所信是如此广大和踏实,它包含生与死,包含绝对的应许——天地大义应许给人的一份公平;但是现在,他发现,他的“天”暗自改变了主意,他不知在他头上运行的“天”已经被“历史”所取代,这是一种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方向的意志,他当然没有机会领会和顺从这个新的“天”,他甚至不知道这个新的“天”是什么,他只能在他的世界逻辑中顽强地要求公道。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 在古老中国的民间想象中,大地的夜晚总是游荡着这样不屈、不散的魂魄,我们曾经相信——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内心最深处的敬畏——那些冤屈的厉鬼郁结了人世的所有悲苦和不公,他们因此不安息,也因此有权向天、向我们索要。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最黑暗的想象在这些严厉、狰狞的影子中惊悸地展开。 这是中国精神中已遭祛魅的一脉传统,它也许还在人心的偏僻角落中活着,但它肯定已经在我们阳光普照的世界图景中消失。但是现在,莫言在《生死疲劳》中让它活了过来,在现代中国的背景下,这个厉鬼森严猛烈地挣扎。 那么,他是谁呢? 西门闹是通行的文学思维无法捕捉的鬼魂,在小说艺术的意义上,他是一个“人物”吗?在哲学意义上,他是一个“个人”吗?他都不是。他是西门闹,但通过转世轮回他又是一头驴、一头牛、一头猪、一条狗、一个猴和一个名叫大头儿的人,每一次新的生命都是新的性格和命运,你无法把他当做“这一个”进行界定,他是“这几个”;你也不能将西门闹和他的几度转世仅仅看做是机巧的结构,“这几个”不仅分担着渐渐稀薄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魂魄、精气贯注。他们中的每一个是“我”,也是“他”,是过去、未来和可能的“我”。 在现代思想背景下理解西门闹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世界观,那么,西门闹就是自然的;在那古老的世界观中,大道运行,万物各秉精气而生,在身体、表象之下,世界有共同、普遍的根源。 这种世界观无疑已在现代以来的观念竞争中落败,但那是仓促、草率的溃败,落日应该有壮丽的余辉,而我们似乎一直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似乎在一夜间,轰鸣的电声遮盖了天籁,古老的乡土沉沦,全球化的大神降临。 但是在这一往无前的变化中,莫言停下来,回头看到了一个巨大空间,这个空间属于他自己,一个对乡土和传统的悲壮命运有着血肉体认的中国作家,一个有着直觉的、身体的旺盛力量的作家,一个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的作家,一个对生命之酷烈、之浩大和渺小有着东方式的执着和坚忍的作家——最后这种品质常常使饱读西方诗书的神经脆弱的知识分子们感到混杂着厌恶和罪感的不适:人怎么能这样?他们忘了,中国人从来就是这么想、这么经验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是脆弱,也是坚忍,是天地无情,也是天长地久,中国作家中,懂得这句话的惟莫言而已。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莫言的兴趣并非历史,对历史叙事的判断、质疑或拆解从来不是他的目的,他对历史的看法并未超出80年代以来的主流论述,他所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xianga.com/cxgj/129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