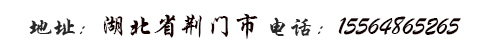莫言走出诺奖魔咒丨仲伟志搜神记
|
白癜风袪白 https://m-mip.39.net/czk/mipso_7007658.html 莫言。年3月,北京 摄影:罗健 莫言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出现在我们面前,单脚停下,然后用一条链子锁,将它牢牢锁在马路边的栏杆上。 张清华端详了一会儿,跟我说,莫言的头怎么越来越大了。 那是年3月,北京北太平庄,第一次见莫言。在此之前,一直想采访这位山东高密老乡,但对他的著作,我只读了几本,没有什么对话能力,屡屡作罢。后来想了个招数,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清华来做“采访嘉宾”。清华也是山东人,我的老朋友,著名的“莫言研究专家”。 那几年,张清华刚从山东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就住在北师大校园里。我离得近,常走过去聊天。当时就有个疑问:北师大校园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乌鸦?这个疑问一直保持到现在。 一次聊到莫言,张清华说,如果国内有一个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莫言。 张清华对各种文类有着驳杂的爱好。他的心中装着一部中国诗歌地理,同时,他长期阅读和研究先锋作家和新潮小说作家,主要包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朔、张炜、王安忆、贾平凹等等。这是风云际会的一代人,他们赶上了历史的大变动,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张清华与他们基本是同一代人,共同的阅历、共同的知识构造、共同的趣味,让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 所以,我认为清华所说应该是靠谱的。 我就照搬了这句话去跟我身边的朋友们说。那些只是从张艺谋电影中知道莫言的人,连连摇头。“仲伟志说莫言会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甚至被人拿来当做一个笑料。这件事,我当时的同事黄一琨可以给我作证。但是黄一琨不知道,这话其实是我从张清华那里学来的。 几年后——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张清华说:“我认为诺奖评委会是非常敏锐的,他们给予了一个最高阐释,或者叫阐释的最高限度,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肯定了莫言的价值。这个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作家都有这个机遇,很多美国的作家、欧洲的作家没有这个机遇,他们的书写都非常个人化,在表现人性方面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领悟,但是他们缺少这种历史的巨大动荡,缺少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和摧枯拉朽的灭亡。” 前些天再去拜访张清华。如今他除了继续教书、带博士,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们引入国际上流行的驻校作家制度,用了五年的时间,在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苏童、西川、迟子建、翟永明、格非、韩少功等10位驻校作家,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影响到校内外大量青年学子,扩展了青年人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张清华说,写作中心的最大诉求,就是推动文学教育,在技术主义时代重建人文精神。 莫言如今担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那里有他的办公室。 旧话重提,我问张清华,你当年怎么那么笃定莫言就能获奖? “哈哈,那时候还算年轻,经常会很狂妄地下点类似的断语。”他说,“不过,因为那几年跟国外很多搞汉学的、搞翻译的常有交流,知道那个时候国外对中国作家了解最多的,就是莫言和余华。这是最主要的依据。你在国内影响大,在国际上没有人知道,你得不了诺奖,这不是基于你个人爱好,咱说了也不算。” 我问:那么谁能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这一次,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个作家,而是说,“我认为中国作家不只莫言一个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这一代作家都应该得,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在是太大。” 好了,我们把话题回到当年对莫言的那次采访。 那是在北师大附近的一个餐馆,我做东,张清华提问。对莫言创作一知半解的我,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听众。 其实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完莫言的全部作品。这不能全怪我,要读完莫言的小说,的确是一个体力活。我粗算过,他的作品总量至少有一千万字,仅是长篇小说,当时就已经有十几部。有几年间,往往是一本还没看完,莫言又出新书了。 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按张清华的说法,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作品是否有足够的量,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作品世界”。现当代作家中,靠一两部作品来立身的作家毕竟是少数,比如鲁迅,更多的人——比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都可谓著作等身。在当代作家中,莫言可谓是最具持续创作能力的作家之一,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上逐渐坠落,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飞行高度,玩着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可以说,由于莫言和他的多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当时,我们想知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是什么力量使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也是一个写字的,那么多字,即便不走心,只用键盘敲,也会累垮我的。如此众多高质量长篇,该耗费莫言多少心神?你看,多年案牍劳形,导致他的头发日渐稀少,脑袋才会显得越来越大。 莫言说,主观上来讲,是太把小说当回事了。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爱都倾注于小说,头脑里面有关小说的弦绷得很紧,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与小说有关的一切,都会唤起他的想象。生活中碰到的事情,与人交往当中的事情,无论形象还是语言的,都会马上记录到他头脑中的小说仓库里,变成小说的素材、创作的动力。 ——把小说当回事,这样的作家并不少,你何以写这么多? 他点上一支烟,烟雾立刻笼罩了那颗硕大的头颅:“这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们这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相对于现在年轻的作家来说,生活经验要丰富一些,不管怎么说,都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是亲历者。像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文化大革命,与‘文革’后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生活给予我们的东西确实非常多。这些东西如果给一般的人,可能就是过眼云烟;但对于小说工作者,这是宝贵的财富,他在不断回忆,甚至因为职业性的习惯,不断强化自己的回忆,写作中回忆,回忆中写作。回忆也属于一种创作,日常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都会触发自己过去的记忆。当下发生的事件跟过去的记忆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新的东西。这能够使我老是感觉有东西可以写。” 莫言写得多,也得益于他的汪洋恣肆。他是一个不太爱惜自己羽毛的作家。很多人往往被名声所累,被过去的成绩所累,举步维艰。而莫言始终保持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状态,不怕失败,不怕被别人说这一部不如以前。“其实你写的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你只有乐意写,才可能有所突破吧。” 尽管在获得诺奖之后,他也曾一度不敢轻易出手,但是还好,他走了出来,“忘掉一切,想怎么写怎么写”。 这番话对于我这个靠码字为生的人来说,真是极大的励志。 在获得诺奖之前的那些年,莫言提出一个观点——“作为老百姓写作”,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引起很多议论。他的核心思想是,既不是站在劳动者的启蒙和拯救者的高度上,也不是站在权力附庸的角度上,更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天然优越感之上,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生命、普通劳动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这样的写作姿态,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 莫言说,“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清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清理的同时,许多作家头脑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具有一种优越感,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理解人生,认为作家的职业就是应该居高临下,变成人民的代言人。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令人血热的口号,但其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本身就是自己地位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而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不是你要替老百姓说话,你本来就是老百姓,你是替自己说话,你个人的痛苦、喜怒哀乐,你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跟大多数人民感受一样的话,从自我、从个人出发的写作,实际上具备了普遍广泛的意义。” 说到这里,作为老百姓,就谈起我们的老家——山东高密。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与莫言的小说多有交集,我母亲被那些民间故事和方言俚语所激励,白发苍苍还立志要写一部小说。她年轻时曾是高密县地方戏专业剧团的演员,在老家名气很大。这种胶东地方戏在莫言的《檀香刑》里叫做“猫腔”,现实中叫做茂腔。说起这一地方剧种的兴衰,莫言如数家珍,甚至手舞足蹈。——那片土地在他身上的印记,越来越不可磨灭,而我对老家却已极度陌生,很多时候,我像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游荡,轻易就会爱上别处的土地。 对此,张清华有一番自己的解读:这是因为莫言“通灵”。因为这一天赋异禀,他与故乡才能骨肉相连,他才会有那么多“奇情异想”,他的作品中才会充满着“大地”的诗意,“你看他的相貌,初看极端质朴,和土地上所生长的事物没有任何区别,仔细看时,却是奇异而神秘的。” 莫言只当张清华在戏说,笑而不语,不时掏出一只牛角梳,拢拢那稀疏的头发。那时的莫言,真是一个心无旁骛、自由飞翔的莫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作家在获得至高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往往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诺奖魔咒”之中,持续写作变得困难。莫言获奖后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调整期。“现在五年过去,我觉得我欠的债也还的差不多了,朋友们的活动我也都参加了,该说话的也都说话了。总而言之,我现在确实应该进入创作状态了。”莫言如是说。 他终于结束了一个忙碌的“公众人物”的状态,找回了写作的感觉,近期连续发表十几篇作品,而且采用了多种文类形式,引起很多议论。一个作家用自己的创作重新引起广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xianga.com/cxpz/12803.html
- 上一篇文章: 荆歌捡漏上
- 下一篇文章: 连慈禧太后都钟情的香气到底是什么